原创李远达:“私自的情理”——明清祭祀文化视域中的《红楼梦》私祭书写
- 文学
- 2024-12-22 18:26:03
- 12
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,断然不可;竟也还要别开生面,另立排场,风流奇异,于世无涉,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。况且古人有云:“潢污行潦,蘩蕴藻之贱,可以羞王公,荐鬼神。”原不在物之贵贱,全在心之诚敬而已。[3]
烧纸结束后,宝玉也明白了几分,便问他:“到底是为谁烧纸?我想来若是为父母兄弟,你们皆烦人外头烧过了,这里烧这几张,必有私自的情理。”“私自的情理”成为宝玉与藕官共同的秘密,也是后续情节展开的充分叙事动力。如果以空间设置合理性与合法性而论,“私自的情理”是区分祭祀场景公共性还是个人性的突出指标,也是私祭场景在《红楼梦》中赖以成立的标志。
桐阶月暗,芳魂与倩影同销;蓉帐香残,娇喘共细言皆绝。连天衰草,岂独蒹葭;匝地悲声,无非蟋蟀。露苔晚砌,穿帘不度寒砧;雨荔秋垣,隔院希闻怨笛。芳名未泯,檐前鹦鹉犹呼;艳质将亡,槛外海棠预老。
最后,更进一步说,叙述者将祭晴雯设置在月夜,正是因为月夜的朦胧笼罩下,人的视觉变得模糊,听觉反而更为灵敏。因此,祭祀完毕后,黛玉在山石背后说“且请留步”以及小丫鬟将黛玉误作晴雯之魂的情节也才稍显合理。由此可见,《红楼梦》所设置之春秋时序与微观时间,皆因时而运事,更以时而生事,进而由这一无可奈何之时转化为不可或缺之境。
忽插入茗烟一篇流言,粗看则小儿戏语,亦甚无味。细玩则大有深意,试思宝玉之为人岂不应有一极伶俐乖巧之小童哉?此一祝亦如《西厢记》中双文降香,第三祝则不语,红娘则代祝数语,直将双文心事道破。
此处若写宝玉一祝,则成何文字?若不祝则成一哑迷,如何散场?故写茗烟一戏直戏入宝玉心中,又发出前文,又可收后文,又写茗烟素日之乖觉可人,且衬出宝玉直似一个守礼代嫁的女儿一般,其素日脂香粉气不待写而全现出矣。今看此回,直欲将宝玉当作一个极清俊羞怯的女儿,看茗烟则极乖觉可人之丫鬟也。[18]
叙述者如此安排调度,宝玉与黛玉之关系在宣叙与窃听之间才显得愈发浓烈,而丫鬟设置之功用也发挥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。
这日宝玉清晨起来,梳洗已毕,冠带出来。至前厅院中,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,宝玉炷了香。行毕礼,奠茶焚纸后,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礼,出至月台上,又朝上遥拜过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。一顺到尤氏上房,行过礼,坐了一回,方回荣府。
先至薛姨妈处,薛姨妈再三拉着,然后又遇见薛蝌,让一回,方进园来。晴雯麝月二人跟随,小丫头夹着毡子,从李氏起,一一挨着所长的房中到过。复出二门,至李、赵、张、王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,方进来。虽众人要行礼,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,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。王夫人有言,不令年轻人受礼,恐折了福寿,故皆不磕头。
(宝玉道):“晴雯到底是个丫头,也没有什么大好处,他死了,我老实告诉你罢,我还做个祭文去祭他。那时林姑娘还亲眼见的。如今林姑娘死了,莫非倒不如晴雯么,死了连祭都不能祭一祭。林姑娘死了还有知的,他想起来不要更怨我么!”袭人道:“你要祭便祭去,要我们做什么?”
宝玉道:“我自从好了起来就想要做一道祭文的,不知道我如今一点灵机都没有了。若祭别人,胡乱却使得;若是他断断俗俚不得一点儿的。所以叫紫鹃来问,他姑娘这条心他们打从那样上看出来的。我没病的头里还想得出来,一病以后都不记得。你说林姑娘已经好了,怎么忽然死的?他好的时候我不去,他怎么说?我病时候他不来,他也怎么说?所以有他的东西,我诓了过来,你二奶奶总不叫我动,不知什么意思。”
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虽然文体有别,但都诞生于乾嘉考据学时代小说知识浓度提升的大背景之下,小说家如何调度知识、思想而为艺术呈现服务,私祭场景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切入角度。当然,明清祭祀文化视域中小说私祭书写的横向比较,那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范畴了。
注释:
[1] 关于《红楼梦》祭祀仪礼的民族属性问题,赵冈的《考红琐记》(台北《中国时报》1980年12月28日)与邓云乡的《<宁国府除夕祭宗祠>诸礼非满洲礼仪辨》(《红楼梦学刊》1982年第1辑)这组论辩文章做了深入细致的辨析。后来邓小飞的《“悬影”不是满人礼仪》(《学术论坛》1982年第6期)和夏桂霞、夏航的《浅析<红楼梦>中的萨满文化》(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6年第2期)等论文均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。
[2] 作为《红楼梦》的经典场景,《芙蓉女儿诔》的诞生在红学界历来备受关注。20世纪70年代末,蔡义江先生《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》对《芙蓉女儿诔》做了深入解析;80年代,张庆善先生在《说芙蓉》(《红楼梦学刊》1984年第4辑)一文中就对曹雪芹将晴雯比拟为水芙蓉还是木芙蓉进行了探讨;林乃初先生的《论<芙蓉女儿诔>的稚嫩美》(《红楼梦学刊》1989年第4辑)分析了该文的艺术特色;从文体学角度看,马凤程先生将《芙蓉女儿诔》与《离骚》进行对照(《<芙蓉女儿诔>与<离骚>》,《红楼梦学刊》1986年第1辑);新世纪以来,张云先生的《<芙蓉女儿诔>的文章学解读》(《红楼梦学刊》2008年第1辑)和王思豪先生的《骚·诔·赋:<芙蓉女儿诔>的文体学演进理路》(《红楼梦学刊》2021年第2辑)分别从文章学与文体学的理论维度审视这篇《红楼梦》“诗赋之冠冕”,尤其是后者认为《芙蓉女儿诔》“打破诔文‘正体’礼制规范”的结论对本文之写作大有裨益。本文由此出发,将《芙蓉女儿诔》的写作情境置于私祭之时空中加以考察,以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。
[3](清)曹雪芹撰、无名氏续: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八回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年版,第1106页。后文引用《红楼梦》原文,不经特殊说明,皆引自此本。
[4] 张寿安对清代礼学及明清礼学转向有过论断:清代礼学家“力斥宋明礼学的‘缘俗’性格”,提倡“以经典为法式”。因此,明清礼学的重要转折是“从‘私家仪注’的‘家礼学’走向‘以经典为法式’的‘仪礼学’。”见张寿安:《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——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82页。
[5] 兰陵笑笑生撰、陶慕宁校注: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五回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829页。
[6] 西周生撰、李国庆校注:《醒世姻缘传》第四十一回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526-538页。
[7] 随缘下士编:《林兰香》第十八回,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,第96页。
[8] 曹雪芹著、脂砚斋评、吴铭恩汇校:《红楼梦脂评汇校本》(下)第五十八回,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,第748页。
[9] 李鹏飞:《试论古代小说中的“功能性物象”》,《文学遗产》2011年第5期,第119-128页。
[10] 吕启祥编:《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(增订本)》下册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年版,第261-262页。
[11] 张一兵,周宪主编:《王伯沆批校<红楼梦>》第2册,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812页。
[12] 曹雪芹著、脂砚斋评、吴铭恩汇校:《红楼梦脂评汇校本》(中)第二十八回,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,第380页。
[13] 曹雪芹、高鹗著;护花主人、大某山民、太平闲人评:《红楼梦(三家评本)》第七十八回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,第1307页。
[14] 李简:《<西厢记>的“春”与“秋”》,《智慧中国》2020年第2期,第84-86页。
[15] 李远达:《“歇午”与“夜宴”:<红楼梦>微观时间设置的叙事潜能与文化意蕴》,《红楼梦学刊》2020年第5期,第76页。
[16] 曹雪芹、高鹗著;护花主人、大某山民、太平闲人评:《红楼梦(三家评本)》第四十三回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,第691页。
[17] 张一兵,周宪主编:《王伯沆批校<红楼梦>》第2册,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 第593页。
[18] 曹雪芹著、脂砚斋评、吴铭恩汇校:《红楼梦脂评汇校本》(中)第四十三回,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,第565-566页。
[19] 张一兵,周宪主编:《王伯沆批校<红楼梦>》第2册,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593页。
[20] 原所贤、暴连英:《试考枫露茶》,《红楼梦学刊》2012年第4辑,第78-82页。
[21] 曹雪芹著、脂砚斋评、吴铭恩汇校:《红楼梦脂评汇校本》(上)第八回,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,第124页。
[22] 曹雪芹、高鹗著;护花主人、大某山民、太平闲人评:《红楼梦(三家评本)》第六十二回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,第1007页。
[23] 张一兵,周宪主编:《王伯沆批校<红楼梦>》第3册,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857页。
责任编辑: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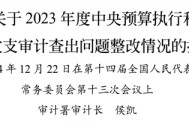



有话要说...